僭越的慾望,凝視分裂的主體 “你為何一直抱著石頭”基宇迴應父親,是石頭一直黏著他。當基宇首次看到石頭,便彷彿被它懾住,說道這真的很有象徵意義。這顆石頭有何魔力?與其說是平平無奇的石頭令基宇欲求得到它,毋寧說是石頭
2021-05-24 18:01:42

僭越的慾望,凝視分裂的主體
「你為何一直抱著石頭」
基宇迴應父親,是石頭一直黏著他。當基宇首次看到石頭,便彷彿被它懾住,說道這真的很有象徵意義。這顆石頭有何魔力?與其說是平平無奇的石頭令基宇欲求得到它,毋寧說是石頭的凝視令他渴望自己成為慾望的對象。
精神分析大師拉康(Jacques Lacan)指出凝視(gaze)並非主體在觀看,而是從客體的位置觀看主體,意味著當主體的慾望投射於客體時,其實無法獲得欲求之物,而得到的總是那個慾望主體自己。主體自身成為他慾望的對象,拉康形容這就是主體總想「讓自己被看到」的慾望。片中石頭首次從盒子顯露時,鏡頭從石頭的角度拍著基宇一臉疑惑的神情,便是客體在凝視主體,揭開基宇作為慾望主體的渴求。
後來基宇舉起石頭,目不轉睛地盯著它,寓意基宇其實在回看自己,渴望自己成為慾望的對象。拉康以「小對象a」(objet petit a)形容這種由主體構成的慾望對象,並指出這終究是徒勞無功的循環,皆因主體永遠得不到欲求之物,而只是不斷追逐由主體匱乏形成的小對象a。
石頭彷彿點燃金家往上流的慾望,令各人為之醉生夢死,甚至有一幕沉重的石頭居然神奇地浮上水面,讓基宇再次抓著它,就如小對象a不斷引誘主體追求這個慾望空洞。但當基宇帶著石頭往地下室時,石頭脫手掉落樓梯,隨之轉化為摧毀金家夢想的凶器。
拉康指出,創傷是主體發現真理的時刻,明白慾望終究是指向主體的虛無。金家的創傷令他們體悟,往上流到頭來是一場虛幻的夢,最終甚麼也得不到,而只有匱乏是最真實。石頭就只是一顆石頭,沒有甚麼象徵意義。

主體的偷窺與客體的凝視構成全片對踰越的慾望。片中每次的偷窺都為主體帶來快感,挑動他們踰越固有的界線。樸夫人一次在梯間窺見基婷令多頌順從、一次窺見管家咳嗽,令她越出相信自己的最後界線,而完全掉進金家設的圈套中。
片中多次形容樸夫人為人單純,而這份「上流」的單純恰恰為她的越界帶來代價,亦成為底層的慾望成因。多惠在樓梯角落窺見基宇與基婷,挑起她的嫉妒而跨越師生的禁忌,主動向基宇表達心意。這個越界預示著對樸家結構的顛覆,象徵欲愛的水蜜桃原是被禁的食物,皆因在樸家年資最久的管家對它敏感,如今禁忌的愛火解放水蜜桃的慾望,將管家從權力位置拉下。
偷窺是主體的欲求,但當偷窺被揭發,則為主體帶來創傷。當金家在地下室樓梯的窺看被揭發,主客關係瞬即逆轉,由偷窺變為被凝視的金家生起羞恥感,驚覺自身其實與管家無異,都是虛空的裸命,而管家夫妻則從被壓迫位置重奪主權的慾望,踏上大廳,對金家報復。

繼承拉康學說的當代精神分析師齊澤克(Slavoj iek)直言,主體從來不是自足完滿,而是被意識形態編織的幻象(fantasy)遮蔽主體的裂縫,令主體遺忘自身原是分裂的。上流的樸家乍看是一無所缺又美滿的家庭,連金先生都稱許樸夫人善良又單純,但隨著故事發展,樸家的完整背後其實隱藏著不少祕密。
從象徵上流身分的大宅埋藏著地下室及寄居其中的管家、金家的計謀,到多頌的創傷與偽裝等,樸家並不如樸氏夫妻想象的典型上層家庭般完滿。事實上,這種上流生活果真令他們活得自在嗎?或許不然。他們的性愛正好揭示對上流意識形態的隱微批判。
影片描述他們對尹司機的疑似古怪性癖感到嘔心,但詭異的卻是這些儼然下流的性癖成為他們性愛快感的來源。
齊澤克指出意識形態建構的象徵界(symbolic order)塑造主體的慾望,以此規訓人的生活,但主體被壓抑的慾望並沒有消失,而是一直藏在潛意識下,在不同時機以倒錯(perverted)或被禁止的方式為主體帶來絕爽(jouissance),顛覆象徵界設立的律則。但當被壓抑的真實(Real)完全暴露,象徵界就會被消融,令主體與自身虛無相遇。當一切祕密在片尾被揭露,樸家便迎來樸社長實在的死亡,及上流身分被摧毀的象徵死亡。

「戀殖」的自虐,寄生的曖昧
「為偉大的樸社長獻上無盡感謝」
影片主旨明顯是關注貧窮問題,但它與其他縷述社會不公的電影有何區別,以致能獨樹一幟?最大的分野是此片對階級關係的獨特描繪,意即導演並無將上層的樸家刻意塑造為萬惡的魔鬼,卻是帶點同情地形容他們的待人處事,反而下層的金家形象更為負面,是名副其實的寄生蟲。
這種非傳統左翼的視角正是意圖呈現階級關係的含混(ambivalence)與曖昧,呼應後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cism)提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複雜關係。後殖民理論家巴巴(Homi Bhabha)指出殖民者利用殖民地圖利時,會為當地帶來現代化的改革,改善人民生活,因而令被殖民者產生「戀殖」的情感。
作為曾被殖民的我們,相信對此深同身受。片中的金家及管家均對樸家有這種「戀殖」情意結,如管家丈夫連死時都向樸社長表達敬意,哪管樸社長根本沒把他當人看待。金先生則形容有錢人如此善良,反而是太太忠淑糾正他是因為有錢才善良,暗指德性(virtue)也無法脫離特定的意識形態,亦間接合理化金家的瞞騙行為。

「戀殖」令被殖民者產生幻覺,以為可與殖民者平起平坐,甚至錯認自己的身分,如基宇幻想與多惠結婚、金家以為大宅屬於自己。當陷入愈深的幻覺,踰越的界限就愈大。金先生在狹小的房間唐突地抓著樸夫人的手,又先後兩次提及樸社長與妻子的關係,突顯被殖民者對自身身分的遺忘。這種無意識的遺忘最終註定為自身帶來危機,就如樸社長多次提及對越界的反感,反映殖民權力不容挑戰,不切實際的幻想只是徒然。「戀殖」的幻覺令被殖民者看不見更宏觀的權力壓迫結構,甚至更令他們為著殖民者賦予的利益與權力,甘願同化成殖民的共謀者,壓迫同為被殖民的一群。
當忠淑得知管家的祕密,同為底層的她非但沒有以同理心向他們施予援手,反而立時意圖驅趕他們,正是體現被殖民者對自身階級的背叛,墮入上層分裂下層的圈套。金家與管家在大廳的赤裸鬥爭,反映為著生存,人也被還原成弱肉強食的動物,彼此浴血相爭,製造仇恨的循環。裸命的自相殘殺是階級及殖民制度下不斷上演的悲劇,也是革命始終未能實現的境況。
片中除了下層的「戀殖」,導演將寄生的主題牽扯到更闊的南韓外交政治處境。上流的樸家其實也寄生在更大的宿主──美國身上,藉以確立自身的位置。樸社長的企業攻佔紐約的報道、多頌對印第安文化的愛好、樸夫人對美國學歷、產品的崇拜及她言談間的韓英夾雜,在在都影射南韓上流對美國的慾望投射,以此建構他們的主體性。有別於《韓流怪嚇》對美國較直接的批判,導演在此片則以上層對美國的戀慕,暗諷當中的權力勾結關係,特別是當全球資本主義雷厲風行,貌似為南韓帶來經濟收益,深層次的貧窮問題卻仍舊惡劣。
除了美國,導演亦在片中觸及北韓的角色。管家指出大宅地下室的設計原意是為了躲避北韓的攻擊,及後管家模仿北韓廣播員,嘲諷北韓無核化的笑話,反映北韓作為南韓的他者,一直被塑造成具有敵意的潛在危機。齊澤克就指出意識形態刻意強化這種他者的陌生性、異質性,令主體將自身的匱乏轉化成對他者的敵意,從而鞏固象徵界的同一性。導演在片中無再深入探討兩韓關係,但加插管家戲仿的情節也許暗示南韓亦是寄生在對北韓的敵對幻象中。

濁世下的清泉,不正常的瘋子
全片幾近將人性最醜陋的一面毫無保留地揭示,結局的「攬炒」亦令人慨嘆,彷彿人類社群的美善早已蕩然無存。雖然影片的主調灰暗,但導演在片中亦留下救贖的碎片,讓我們一瞥盼望的曙光。這份盼望在哪?就是片中唯一的小孩──多頌。多頌可謂全片未受汙染,保留人性純真的異類,而這份單純亦使他擔當劇情推進與轉折的角色。
從樸夫人口中,我們得知原來多頌是首個與管家丈夫相遇的人物,可謂最早被真相抓住的人,而這個發現亦為他帶來創傷,呼應拉康提出創傷於主體發現真理時發生。這個創傷令多頌彷彿成為全片洞悉全局之人。他首先發現金家氣味相似,為電影引入氣味此符號,然後是他將樸家往露營的消息告知管家,引發揭開大宅祕密及金家與管家鬥爭的張力敘事。不知是刻意或偶然的編排,多頌又堅持在雨中紮營,令他窺見樓梯閃燈的摩斯密碼信號,並因著他的生日派對,令真相公諸於世,將劇情帶到高峰。
多頌在片中被視為古怪、調皮,甚至是「精神分裂」,但他卻是唯一在全片看清一切之人。這些不正常的標籤反諷地映照出誰才是真正瘋狂之人。多頌的純潔、無辜令他在片中顯得格格不入,被權力爭競的世界排除在外,但他的誠實將其他角色的偽裝、慾望、迷失揭露,儼然人性的敗壞都逃不過孩童清澈的眼目。延續前作《玉子》的設定,導演也是以孩童的真誠對比成人世界的腐敗,反覆寓意老練的成人應反撲歸真,如耶穌所言,學像小孩子才能進天國,認清權欲試探背後的真相,放下虛妄的追求,尋回並接受破碎、失落的本我,哪怕這一切逆流的真理令人恐懼,為主體帶來創傷。

「攬炒」絕路下的盼望?
「攬炒」的結局不致完全「攬炒」,導演沒有「賜死」所有角色,彷彿遺留一絲的可能。走過上層的幻想與撕殺後,曾問管家丈夫有何計劃的金先生,諷刺地逃回地下室自我囚禁。命運早有定局,管家當初剪掉大宅外閉路電視的天線,成就金先生這個自我懺悔的機會。這個結局尤如卡繆(Albert Camus)筆下的薛西佛斯神話一樣,地下室的荒謬生活,讓金先生認清人生本相,在荒謬與無意義的循環中積極反抗,堅持寫信給兒子。基宇被石頭所傷後,意外地被救回,但行為怪異,失常地笑。
與多頌一樣,創傷讓人從幻象中甦醒,成為瘋子看清現實世界的「正常」比瘋癲更瘋癲。基宇後來發現父親的蹤影,意圖買下大宅拯救父親,卻始終是南柯一夢。這個結局可被理解為絕望的寫照,表達他只是空想救回父親,但也可詮釋為基宇不再陷入虛空的幻想中。片尾放石頭到水中的一幕,象徵著他認清真相,不再被慾望矇蔽而迷失。片尾的鏡頭刻意呼應片頭的鏡頭,由上而下影著身在地下室的基宇,有別於片頭的陽光,片尾的下雪晚上代表他歷盡鉛華,不再被陽光下的眩目、夢幻所騙,踏實地回到起點,重新計劃前路。影片在此結束,到底基宇真的努力賺錢救父,還是止於空想?導演刻意留白,讓觀眾自行想象。

階級鬥爭是底層擺脫命運的出路嗎?從結局的「攬炒」可知導演對此不抱期望,皆因這終究會陷入另一仇恨循環。導演並無指引光明可見的出路,階級依舊難以撼動,壓迫從沒停止,唯有重尋潛藏在人心深處的美善種子,才是捍衛世途崩壞的最後防線。當世界迫瘋我們,成為瘋子或許是唯一選擇。
相關文章

僭越的慾望,凝視分裂的主體 “你為何一直抱著石頭”基宇迴應父親,是石頭一直黏著他。當基宇首次看到石頭,便彷彿被它懾住,說道這真的很有象徵意義。這顆石頭有何魔力?與其說是平平無奇的石頭令基宇欲求得到它,毋寧說是石頭
2021-05-24 18:01:42

姐姐,你可知道你的名字,解釋了我的一生。 看完《我的姐姐》,大腦暫時無法思考,只知道全片貫穿的是滿滿一屏幕的心酸,姐姐安然在道德與自我間的掙扎,弟弟安子恆在新環境中的稚嫩童音和聲聲哭泣。 “長姐如母”這四個字
2021-05-24 18:01:33

囧媽 “你為什麼要鍥而不捨地改造我呢?都這麼多年了,難道你還沒有意識到我不是你想的那個人嗎?”這句話在電影《囧媽》中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徐伊萬的妻子對他們的婚姻心灰意冷,一次是徐伊萬對他的媽媽忍無可忍。兩段雷同的.
2021-05-24 18:01:28

李煥英頭上綁辮子的牛皮筋、連成片的金黃水稻、用票買家電……這一個又一個的細節設置無疑從細微之處揪住了李煥英那一代人的群體記憶,從而擴大了該影片的受眾群體。 此外,笑點和淚點相夾雜也是其特點之一。影片以喜
2021-05-24 18: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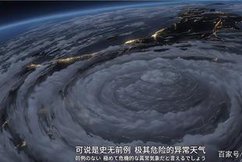
…這樣一部電影,或者說新海誠所有的電影,可能最怕的一種影評便是動輒就總結中心思想,總結出一種XX樣的精神,這樣的話,真是太摧殘了。我謹認為,一部優秀且豐富的文藝作品,一定存在許多視角可以審視,但沒必要非得人為歸納出一個
2021-05-24 17:00:45

後來還說自己進入娛樂圈就是因為長得帥被星探發現了。才勉強把氣氛搞得活躍一點。其他人才敢配合地笑一笑。雖然說這次是汪蘇瀧圓了場子,但是之後不能每一次都這樣,汪蘇瀧也是來參加節目的,不是作為主持人調節氣氛的。節
2021-05-24 16:01:32